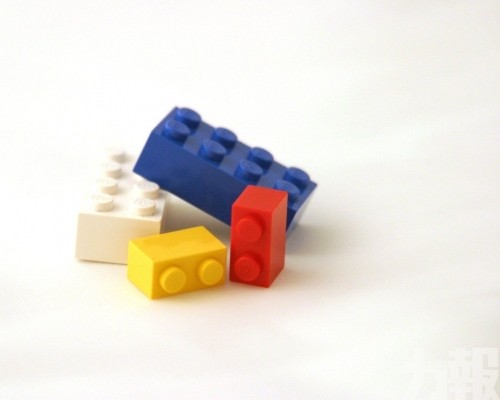我在經濟預測行業工作了近50年。我的職業生涯始於上世紀70年代初華盛頓特區美聯儲研究部門,後來又在華爾街幹了30多年。十多年來我在耶魯大學工作——仍時不時地涉足預測,但主要從事教學、寫作和演講。
在這麼長時間裡,我的預測紀錄好壞參半。我在美聯儲做過幾次值得銘紀的預測,我警告過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急劇衰退和後期棘手的通貨膨脹。但最令我自豪的是與拉裡.斯利夫曼(Larry Slifman)合作構建了美聯儲的第一個「黑匣子」預測模型,我相信它在今天仍然在廣泛使用。我們連軸轉地工作了幾個星期,編寫互相連接的基於電腦的報表(當時還鮮為人知),以此代體此前在門羅計算器(Monroe calculator)上手動完成的月度一步反覆運算。我們所謂的判斷方法是美聯儲著名的大規模計量經濟模型的針鋒相對(point-counterpoint)。
我的華爾街生涯更富戲劇性。我不斷地預測,但更關注大局發展,如 20世紀80年代末的公司債務和重組、 90年代的 生產力辯論 、21世紀初後危機世界的全球恢復,以及我當時的「最愛」—— 中國及其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我的華爾街預測紀錄足以保證我的摩根士丹利工作無虞,儘管有幾次頗為僥倖。
試圖預測利率是我最不喜歡的工作。這有充分的理由。我還紀得我走進老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會議室,看到一張我前任得債券市場預測圖表倒置在地板上。我決心避免這種命運。當我最喜歡的債券交易員開始叫我「飛鏢人」時,我做出了一個管理決定,從這件事上脫身,並雇傭一位利率策略師。我想是適者生存。
去年夏天,當我從預測崗位退下,寫了一篇如今令人難忘的題為《美國即將二次探底》的文章時,我應該頭腦更清醒一些的 。我認為,疫情後的反彈——在2020年第三季度GDP年化增長達到創紀錄的33%,此前的二季度則大幅萎縮了32%——只不過是數字上的起伏。
但這種敏銳的洞察力並不是重點。我接著強調,新生的復蘇很可能因復發而流產,就像二戰結束以來前11次衰退中的8次那樣。幾個月後,我被經濟指標「打臉」,但我仍然心安理得地犯了臭名昭著的預測錯誤:給出一個日期。實際上,我寫道,未來二次探底可能會發生在2021年年中。
我職業生涯中最糟糕的預測錯誤?看起來確實如此。我尋找的復發並未發生,反而人滿開始普遍談論無限繁榮。我的訓練有素的摩根士丹利後輩們敢說且正確——他們預測新冠疫情衝擊後將出現V型回擊 ——現在他們認為2021年上半年美國經濟年化增長率將接近10%。完全不是我——他們此前的團隊領導人——所預期的探底。如果我還在位子上的話,我會再次因為擔心飯碗不保而驚出一身冷汗。
華爾街的預測者很快學會了責任規則。與債券和股票交易員一樣,「市價計值」思維迫使經濟學家,有時甚至市場策略師,都要承擔智識責任(intellectual accountability)。這時候,你應該有一個有說服力的分析框架告訴你出了甚麼問題以及為甚麼會出問題。
二次探底有三個因素:歷史先例、頑固的脆弱性,以及再次發生衝擊的可能性。此前的商業週期歷史站在我這邊。由於就業和實際產出仍遠低於疫情前的峰值水準——尤其是最重要 服務行業的面對面活動——似乎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來認為存在頑固的脆弱性。最後,隨著11月、12月和1月初新冠感染數量再度激增,美國約 四分之三的州採取了部分封鎖,新的衝擊也近在眼前。綜合起來,我的結論是,二次探底只是時間問題。
那麼,發生了甚麼?
基本上,這種衝擊是短暫的——原因也有三:疫苗、人性和拜登經濟學。美國人踴躍接種,新冠感染率 跌至1月初峰值的26%。這一趨勢,再加上疫苗接種迅速加快,意味著比預期更快地建立群體免疫,並迅速結束疫情。其次,不耐煩的美國人和他們的順從的政治領導人不顧令人擔憂的新冠病毒新變種,正在打破建議的公共衛生限制。第三,財政閘門前所未有地洞開 2020年底的9,000億美元一攬子計畫 ,3月份的1.9萬億美元 美國救援計畫 ,以及現在提出的2萬億美元以上的被稱為「美國就業計畫」額外基礎設施刺激。
隨著疫情結束近在眼前,所有這一切變成了強力順週期財政刺激,再加上持續前所未有的貨幣寬鬆,使得經濟繁榮成為不二之選。去年年底探底的經濟指標,如今已以報復性反彈。
最後,科學、政治和不屈不撓的人類精神的合力,讓我特立獨行的二次探底預測成為笑話。這不是我第一次預測錯誤,但它可能是最「耀眼」的。 說「責任在我」是輕描淡寫。還是回到象牙塔比較好。


史蒂芬.羅奇
耶魯大學教員、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董事長,著有《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