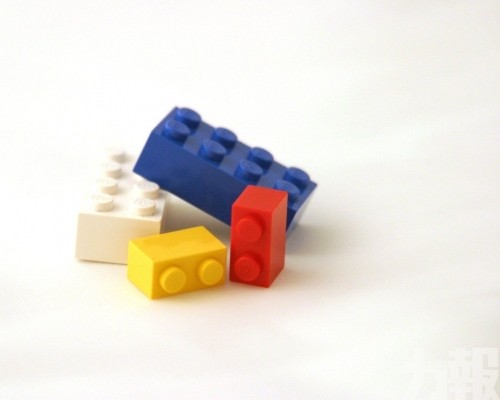魏尚進曾任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及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金融及經濟學教授
發自紐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任期內曾多次提高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從他2017年1月上任時的平均3%左右提高到了2019年底的20%以上,目前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的平均關稅基本與美國在1930年代初根據《斯穆特-霍利法案》對世界其他國家徵收的關稅水準持平——在許多經濟學家眼中正是該保護主義法案導致了嚴酷的大蕭條。如今喬•拜登總統正在扭轉特朗普的多項政策(包括對歐洲商品徵收的進口關稅),同時也必須決定是否要移除其前任的對華關稅。
拜登此舉並不是為了維護中國工人或企業的利益,尤其是他需要保護自身免遭對中國這個美國全球主要競爭對手過於軟弱的指責。但他有三個更有力理由去拋棄這些關稅:它們傷害了美國的工人和企業;未能減少美國整體貿易逆差;也有證據表明其進一步削弱了對全球經濟規則的尊重。
在美國經濟學家實施的所有實證研究中沒有一項表明特朗普貿易戰對美國家庭或企業有利。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瑪麗.阿米提(Mary Amiti)、普林斯頓大學的史蒂芬.雷丁(Stephen Redding)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大衛.威恩斯坦(David Weinstein)研究了特朗普在2018年期間對中國商品的六次加稅——這導致被徵收10%以上關稅的美國進口商品比例從3.5%增加到了10.6%。與特朗普及其高級貿易官員宣稱的相反,更高的關稅幾乎全部轉化成了美國消費者所支付的更高價格。
與此同時,美國從其他國家進口的類似商品也因關稅上漲而變得更加昂貴。因此雖然聯邦政府徵收了額外的關稅,但這只是把錢從美國家庭轉移到了美國財政部。其他各項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由於中國商品的受眾大多為美國的中低收入家庭,特朗普的關稅實際上成為了一種累退稅,導致美國本已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進一步傾斜。
同時中國對美國商品的報復性關稅也導致了美國的額外經濟損失——比較明顯的就是汽車等耐用品的銷量減少。紐約大學的邁克爾.沃夫(Michael Waugh)發現美國那些受中國貿易報復影響較大地區的汽車銷量有所下降(約15%),表明當地家庭收入減少,同時這些地區的就業率也有所下降。
雖然美國一些與中國進口產品存在競爭的行業獲得了某種保護,但這一好處卻被使用中國原材料的部門——包括服務業和製造業——的就業崗位減少以及美國對華出口下降導致的就業崗位減少抵消掉了。
此外美國的貿易平衡狀況也並未因特朗普關稅而改善。2019年美國對華的雙邊赤字與2016年——奧巴馬總統執政的最後一個完整年度——基本相同(約3,450億美元),這表明美國對華出口和從中國進口同樣都減少了約100億美元。
這種模式也延續到了2020年。雖然雙邊逆差降至3,110億美元,但部分原因是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減少了美國的整體進口。而根據兩國“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美國對華出口從2019年的1,070億美元上升到了2020年的1,250億美元,這一數字與2018年的水準相近,但低於2017年的1,300億美元。
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的較高關稅只是令部分產品的進口轉移到了其他國家,而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平衡狀況其實不太影響美國人的福祉,美國的整體貿易逆差在2020年上升到了12年來的最高點,體現了美國國民儲蓄相對國民投資的不足。
雖然中國可以在減少自身貿易壁壘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但這些都不是造成其貿易順差的原因。事實上我與鞠建東和施康的研究就表明是中國在2000年代初的開放進口推動了其整體貿易順差的上漲。
有些人認為美國是出於國家安全考慮而減少對華貿易依賴,但美國擁有比其他所有國家都更多的國家安全工具,因此不需要依靠關稅去在實現這類戰略目標。事實上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的做法應該是在世界貿易組織宣導改革以取締那種將關稅用於非經濟目的行徑。
廢除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對重振全球貿易體系的信心至關重要。2020年9月,一個世貿組織爭端解決小組裁定美國的關稅違反世貿規則。美國原本有權對這一裁決提出上訴,但特朗普政府在前任法官任期屆滿後拒絕確認新法官人選,致使該機構因法定法官人數不足而失去效力。
無視世貿組織裁決可能會削弱拜登政府強化基於規則的全球體系之宣言的可信度。但鑒於特朗普的關稅已經下達,美國是否應該試圖從中國那裡得到一些承諾以換取放棄關稅?
如果拜登能夠獲取一些有用的東西,比如將中國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單邊承諾轉化為更具約束力的國際承諾,他就應該這麼做。但是特朗普關稅留存的時間越長,美國的中低收入家庭就得在更長時期內受壓。正如19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一樣,特朗普關稅的持續存在將不利於拜登實現包容性經濟復蘇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