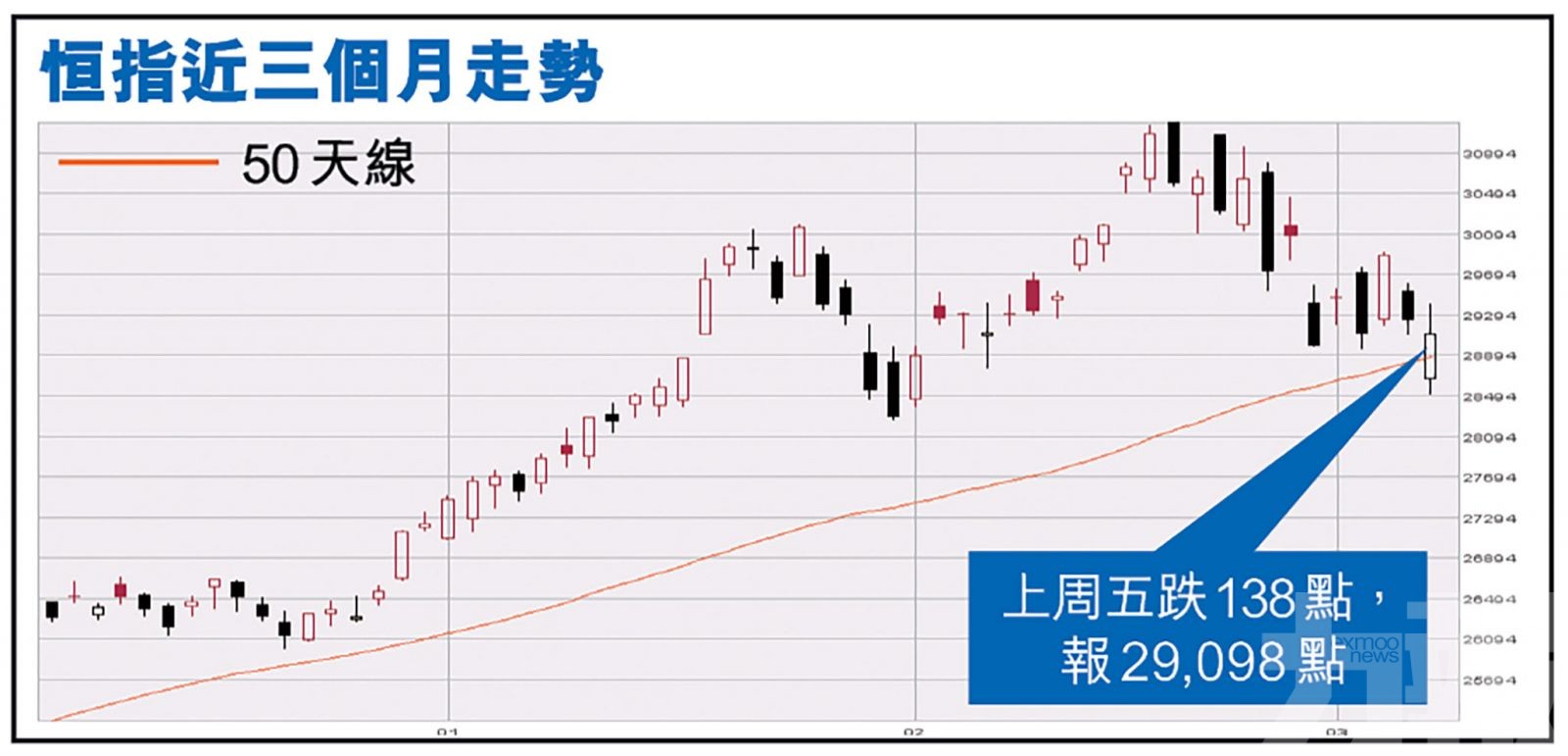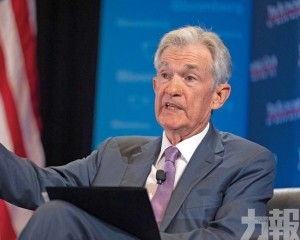發自劍橋—美國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計劃正在引發一場關於更高通脹會否迅速來臨的激烈辯論。由於預期美聯儲(也是事實上的全球央行)將被迫加息進而刺破全球資產價格泡沫,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和抵押貸款利率都有所攀升。但縱使市場可能高估了2021年的各類短期通脹風險,卻未能充分認識到諸多長期性危機。
有一點是相當明確的:眼下和可預見的未來都必然需要大規模宏觀經濟措施來提供支撐。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更為嚴重,美國部分行業依然深陷絕境。盡管新冠疫苗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央行獨立性和全球化都遭舍棄,那麽真正的通脹風險就將顯現。雖然政策制定者有理由在短期內對經濟持續覆蘇下刺激措施和消費者現金儲蓄推動的需求爆炸性增長表示擔憂,但由於現代發達經濟體的物價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變動極為緩慢,因此通脹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間暴漲。即便是許多富裕國家通脹達到兩位數(英國和日本通脹均超過20%)的1970年代也是醞釀多年才全面爆發的。
這主要是因為物價和工資的上漲速度與勞動者和企業對經濟基本通脹動態的觀感之間存在極為緊密的聯系,換句話說就是當前的通脹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長期通脹預期的影響。
這個推理看似有點循環論證的意味,但卻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由於擔心丟失市場份額,許多行業的企業並不願意過大幅度地提高價格。因此如果央行能夠成功地將長期通脹預期「錨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那麽就可以遏制任何長期通脹爆發。而如今多年的超低通脹已經牢牢紮根在了公眾心態之中。
這一切都意味著即便經濟迅速實現正常化,被壓抑的需求和大規模財政刺激也不會當即引發通脹飆升。但如果政客們損害央行獨立性並阻撓政策利率的及時正常化,那麽再怎麽根深蒂固的低通脹預期也會被消磨掉。
而另一個長期通脹風險則更為隱性卻可能更加難以防範。與30年前相比如今許多人都對全球化有所質疑,這主要是因為有證據表明富人從全球化中攫取了過大比例的利益。一方面股市飆升,另一方面勞動力在經濟總量中佔據的份額卻不斷下降。而許多旨在為勞動者奪回更多利益(比如推動工會化和對離岸外包設置障礙)的建議措施都必然會遏制貿易。
全球化的逆轉可能會對通脹產生重大影響。正如美國總統拜登最近呼籲盡快增加本國基礎設施投資時所警告的那樣,許多西方人擔心中國會「吃掉我們的午餐」。這或許有點道理,但西方人也應當認識到中國人才是全球制造業中做午餐的那個廚子,不然的話這頓飯的成本只會更高。
從更廣泛意義來看,從1980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各國央行抑制通脹的努力都大大受益於同一時期的超級全球化進程。許多消費品的價格都被與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以及技術進步所大幅拉低了。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多種物價的明顯下降,中央銀行家們還能借助貨幣政策以外的各類手段去相對輕易地壓低民眾的長期通脹預期。但當我在2003年的一次大型央行行長會議上用一篇題為《全球化與全球通脹不足》的論文指出這一點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並不樂意將一部分功勞歸於全球化。
現在情況可能會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尤其是鑒於國會兩黨在挑戰中國的必要性上所達成的強烈政治共識。而拜登政策的實質內容或許也不會像許多國際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迅速或徹底地與前總統特朗普的政策做切割。但就算美中兩國能彌合當前的分歧,全球化的影響也注定會逐漸減弱,部分原因——正如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瑪諾基.普拉罕(Manoj Pradhan)所有力論證的那樣——是人口構成因素。比如中國就預計會在未來20年內減少2億勞動力。
既然如此,市場是否應該對潛在需求激增推高通脹和利率,進而導致資產價格全面下跌而感到恐慌呢?從短期來看大可不必,甚至各國央行可能還會在一年後認真考慮實施深度負利率以重振通脹和需求。但如果通脹能在低迷如此之久之後的幾年內攀升到目標之上倒也不是壞事,不過更長期的通脹風險要比市場或政策制定者似乎意識到的更偏向於上漲。

肯尼斯.羅格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