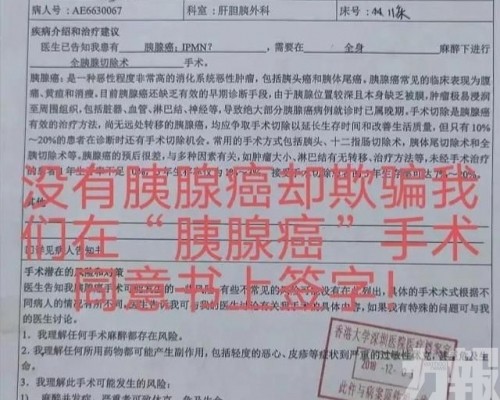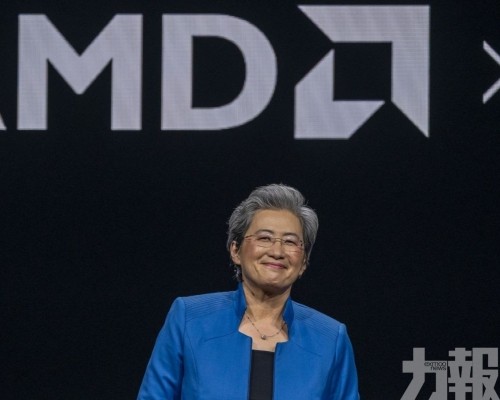劍橋—未來兩年里,世界各地的經濟復甦,就像新冠疫情疫苗的分配一樣,無法做到均衡。盡管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經濟風險仍然深重,這樣的情況不僅適用於即將面臨債務問題的前沿經濟體,還適用於貧困日趨嚴重的低收入國家。目前,新冠病毒遠沒有得到抑制,民粹主義盛行,全球債務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政策常態化進程可能會不平均,這樣的情況十分危險。

這樣說不是為了否認過去一年中所有的好消息。有效疫苗在最短時間內問世,比大多數專家原本預測的早得多。隨著大量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出回應,疫情有望走向終結。而且公眾已經學會如何更好地應對病毒,不管有無國家權力機關的幫助。
但是,盡管全球經濟增長結果已經比人們在疫情早期預測的好得多,目前的經濟衰退仍然是災難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美國和日本將在今年下半年才能重回疫情前的生產水平。同樣,歐元區及英國將在2022年才能達到這一程度。
中國經濟卻遠超其他國家,預計到2021年底,中國經濟將比2019年底增長10%。但相反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回到疫情之前的發展水平。據世界銀行估計,到2021年底,新冠肺炎疫情伴隨著大規模的食物緊缺,將會導致額外的1.5億人陷入極端貧困。
這樣差距懸殊的表現與疫苗供應的時間安排有很大關系。在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疫苗預計將在2021的年中大規模使用,但在更貧困的國家,人們可能要等到2022年或者更久。
另一個影響因素,是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間在宏觀經濟支持層面的驚人差距。新冠危機期間,發達經濟體中,額外的政府開支以及減稅幾乎平均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3%,而貸款和擔保金達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12%。相反,在新興經濟體中,增加的政府開支和減稅大約只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4%,貸款和擔保金只佔到3%。對於低收入國家,直接的財政支持只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5%,而擔保金幾乎為零。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相比於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擁有相對穩健的資產負債表。但在危機期間,但這些新興經濟體擔負了絕大多數的私人債務和公共債務,並因此變得更加脆弱。要不是當時發達國家提供了接近於零的利率,許多新興經濟體都將會深陷困境。即使這樣,當時仍發生了一連串的主權違約事件,其中包括阿根廷,厄瓜多爾及黎巴嫩等國。
實際上,新一輪的「縮減恐慌2.0」非常容易出現問題,如果它發生了(或者說,當它發生之際),遭受衝擊的將不只是新興市場。2013年的「縮減恐慌」發生,是因為美聯儲當時開始暗示,有朝一日它將使其貨幣政策正常化,這導致大量資金從新興市場中外流。而這一次,美聯儲極力暗示,在長時間內它不計劃提高利率,它甚至引入了一個新的貨幣框架,該框架保證了美聯儲將持續「加緊油門」,直到失業率達到極低水平。
這樣一種政策完全合理。2008年後,我一直認為,在一個債務水平高且生產水平不理想的環境下,如果允許通脹率暫時高於美聯儲定下的2%的目標,這其中利遠遠大於弊。畢竟,最近一年內,美國已有900萬人失業。
但如果美國在今年夏天之前完成了其疫苗供應的目標,並且新冠肺炎病毒突變得到了抑制,美聯儲很有可能放棄其零利率政策,大幅提高利率。這種情況很有可能發生,因為美國人民已經積累了巨額的儲蓄儲備,這一方面由於資產價格上升,另一方面由於許多人選擇將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存進銀行。
世界各國的超低利率政策有助於預防長期的負面後果,但對於包括「科技巨頭」公司在內的許多大公司來說,這些他們並不需要的經濟支持卻在幫助他們大幅擡高自己的股價。這必然會激起民粹主義者的憤怒(從一些美國政客對最近「遊戲驛站」股價戰的反應就可以窺知一二)。
目前,通脹率可能會持續處於低水平,但如果需求猛增,也可能導致通脹率升高,從而使美聯儲比目前計劃提前提高利率。這一舉措給資產市場帶來的漣漪效應將區分出強者與弱者,並且對新興市場的打擊尤其嚴重。同時,各國的決策者(甚至是美國決策者)最終將不得不接受破產和重組的情況增多。經濟覆蘇的浪潮必然會來,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會「水漲船高」。

肯尼斯•羅格夫
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